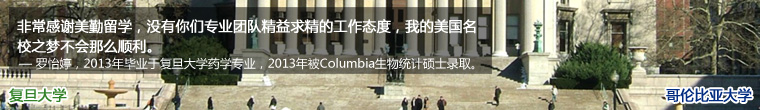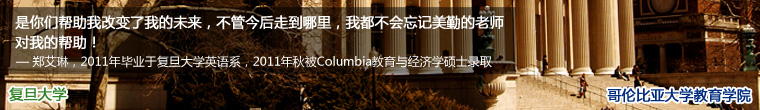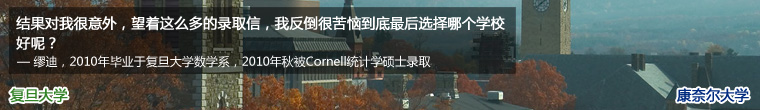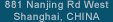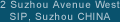杜克大学细胞生物学系王帆教授访谈(2)
吴巍:理查德阿克塞尔是一位神经生物学领域的世界著名学者,可以想象进入他的实验室难度之大。您是如何打动这位世界级学者的?
王帆:理查德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他看上去很凶。(笑)所以大家都很怕他,新学生可能都不太敢去找他。有几个学生给他发了电子邮件,说想去他实验室实习,他没有回信,于是学生们都陆陆续续的打了退堂鼓。刚才说过我听了理查德的一堂课,下课以后我就追上去和他说,“阿克塞尔博士,我能不能到你的实验室作一个实习?”他就回头看了我一眼说,很严肃的说了一句:“从来没有人这么叫过我”。(笑)然后他就问我想加入他实验室的原因。这个原因有好几个。一个刚才提到了,他课讲的很好。第二个就是他非常有名气,学生都很敬佩他。再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系开设了一个讲座系列,从世界各地请来优秀的学者作学术报告。学生在报告以后可以和这些学者座谈。有一次,有个学者在和我们座谈的时候就问,“你们这里有没有来自理查德阿克塞尔实验室的学生?”。当时恰好没有,这个学者就接下去说,理查德太聪明了,他克隆嗅觉受体的工作简直是漂亮的让人难以置信。正是这个学者的这番话促使我去读了理查德阿克塞尔和琳达巴克的那篇经典文献,从此我就被理查德的智慧折服了。所以我并没有特别的想用什么办法去打动他,当他问我为什么想去他实验室实习的时候,我就老老实实的讲到了上面三点,理查德也就高兴的同意了。
吴巍:理查德阿克塞尔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一位博士后俞从容写了一篇文章《与诺贝尔奖得主共事》,其中就讲了很多关于理查德阿克塞尔的故事。那么能请你谈谈您对理查德的印象吗?他是怎样指导你的科研工作的?
王帆:谈到理查德,那真是有太多太多的回忆了。我可以几天几夜的和你谈论他,但是你要让我一句话总结出来是很难的。可以说理查德是一个绝对的天才,独一无二。他的那种影响是潜移默化,根生蒂固的。他从来不指导试验的细节,而总是高屋建瓴的提出整体设想。
我觉得他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他对科学的洞察力和渊博的学识。他非常博学,分子生物学的造诣炉火纯青。在他面前,我当时觉得自己非常的渺小。(笑)理查德经常在实验室和我们聊天,我记得有一次他突然问我,你有没有读刚刚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那篇关于IGF2基因印迹的文章?那时候我科研工作很刻苦,天天做实验做到很晚,多多少少就疏忽了文献的阅读,那些不是本领域的文章就读的更少。所以我就回答说没有。理查德就坐在那里把这篇文章娓娓道来,还告诉我们这篇文章为什么有意思,还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够好,未来的研究方向又是什么。我是完完全全的惊呆了,这个经历就让我知道了要成为一个好的科学家,不能只是看到眼前的这点东西。对知识要有广泛的涉猎,对本领域外的知识也要知道一些,这样才会做到融会贯通。理查德每每看到好的文章,就会在实验室和我们讨论。我受到的很多教育都是理查德通过这个方式给予的。为了博得理查德的欣赏,实验室的人后来都喜欢去读最新的科研文献,然后去和他探讨。我也是一样,于是乎不知不觉地就读了很多文章。有点像和武林高手过招的感觉。(笑)他教你一招,你就知道自己差的很远,然后到一边去修炼内功,过几天不服气了又再去过一招,还是差得很多。这样一来二去,你的功力也就提升了。
理查德对我的影响还在于他重塑了我的哲学观。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严肃的思考过最本质的哲学问题。比如说,什么是意识?人类的思想从何而来?理查德对这些抽象的哲学问题很感兴趣,他会把这些深奥的问题具体化,并且试图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去寻求答案。和他一起共事,你会感到你所从事的科研工作不仅仅只是在解决一些很琐碎的具体问题,而是在为了一个很伟大的目标,为了一个很崇高的理想在奋斗。
吴巍:您的博士生涯真是一段幸福的时光。能否请您结合自己的个人经历给博士生选择实验室提一些建议?
王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兴趣。理查德的研究让我觉得激动人心,所以我博士读的很开心,从来不觉得自己是被逼着刻苦工作。在这五年中,我读了很多,想了很多,真正的在科学领域入门了。这种感觉很好。事实上,在选择实验室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预测博士生阶段的课题能否获得成功的。你是做的顺,还是不顺,没有人能保证。科研就是这样,很难预测未来的成败。如果对自己的课题失去兴趣,那是非常痛苦的,甚至会觉得寸步难行。反过来,如果你有兴趣,那么即使是两三年都没有文章发表,你还是会很有自信地去找出办法来解决问题。一句话,兴趣让科研充满快乐。
吴巍:1998年博士毕业以后您去了马克特希尔拉维尼的实验室作博士后,马克后来2003年的时候去了工业界,成为了Genetech公司资深副总裁。神经生物学泰斗,诺贝尔奖获得者埃里克坎德尔(Eric Kandel) 对他的评价是“马克甚至可以领导美国,他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从他身上您学到了什么?
王帆:你说得没错,马克对实验室的经营很有心得。他会花时间来确保实验室的每个人都过得很开心。他招来的人都有很好的团队精神,他觉得“人和”是极其重要的。另外一点就是,马克是很实际的一个人,他总是想方设法的给实验室的所有人找到一个可行性很高的课题。
刚才提到了理查德对我的很多好的影响,但是,理查德对我也有一点“坏”的影响。在他的层次,他可以做非常有风险的,时髦的,有创造性的实验。他可以接受失败的打击,只要试验室总体课题的成功率高就好了。从理查德实验室毕业以后,我觉得我有点冒进了,选课题的时候太敢于冒险了。这样在博士后阶段就吃了一点亏。我博士后前期做的课题,非常前沿,有长远意义,但是当时只有很少的背景研究。虽然我做的很辛苦,却三年多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个时候马克就和我说,“你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别的课题?像琳达巴克那样能在博士后期间九年如一日不计得失地做一个课题的人是很少见的。大多数的人需要得到正反馈,如果你很长时间都没有成果,你可能会逐渐对科学丧失兴趣的。你可以先做一些别的容易一点的课题,得到一些结果,这样你心里可能会高兴很多。”马克说得很对,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承受多次失败的打击。坚持不懈固然重要,但是如果科研真的那么辛苦却鲜有收获的话,可能很多人就会选择放弃。我听从了马克的建议,换了一个课题,后来就进展的很顺利。所以我觉得马克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他知道怎样让实验室的每个人个体利益最大化,从而激发他们的斗志。我现在管理自己的实验室就是以马克为榜样,我清楚地知道我的学生和博士后需要成果。我既要鼓励他们去做有风险的有重大意义的课题,同时也要给他们想好一个安全的课题作为退路。所以说我的两个导师都对我的成长至关重要。理查德教会了我怎样做科研,马克则教会了我如何经营一个实验室。
吴巍:刚才提到了您在一个课题上花了三年多的时间,却没有得到什么成果。能告诉我们当时的心情么?您又是如何克服困难,很快在另外一个课题上获得成功,并发表了一篇《细胞》论文的呢?
王帆:我先从当时的课题设计谈起。博士毕业以后,理查德说,你博士后期间最好不要接着做嗅觉方面的研究。因为虽然你在嗅觉领域已经驾轻就熟,但是这样的训练对一个科学家来说是不够完整的。最好找一个其他方向,这样可以拓宽自己的视野。我对感觉系统很有兴趣,博士后期间就选择了躯体感觉领域。躯体感觉系统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它包括痛觉,触觉等等。我们知道在大脑躯体感觉皮层有一个复杂精细的体表感觉投射地图。那么这个投射地图在发育过程中是如何形成的呢?有什么分子机理驱动这个过程呢?科学界对此一无所知。所以我就想做这方面的研究。马克实验室的研究领域是发育神经生物学,主要研究神经细胞突触定向生长的机制。于是我和马克商量了一下,他就同意我到他的实验室做这个课题。
结果我们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因为当时基因组计划还没有完成,大量的基因还没有被发现。我们这个课题就等于说要在无数的可能中去搜寻某些个候选基因。希望这些基因在躯体感觉神经元定向生长的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这个实验过程有如大海捞针,我们尝试了无数的实验技术,但不幸最后都碰了壁。后来马克就果断的让我换了课题。那段时间工作很辛苦,自己又刚刚怀孕。古人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发现即使有了远大的目标,还是有很多“近忧”。看到实验室别人发文章,而自己什么成果都没有,真挺难受的,当时也只好“感情要粗糙一点”了。(笑)好在我这个人不是特别容易担忧。那个时候我还是强迫自己对未来抱有信念,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挺过这个艰难时期。后来就“柳暗花明又一村”,换个课题,运气一转,就顺利做成了。